
又一次踏進(jìn)海寧袁花鎮(zhèn)郝山房,整修后的金庸故居靜穆如昔。展廳里添了一壁新書(shū)跡:為母校海寧中學(xué)的題詞、送給《南湖晚報(bào)》的橫披、替鹽官觀潮景區(qū)題寫(xiě)的楹聯(lián)……紙墨雖新,卻帶著舊式文人的溫厚。游客多沖“武俠”而來(lái),臨走卻被一行行挺拔的字拽住腳步——原來(lái)查大俠的“第二重江湖”在這張張宣紙里。

一、舊學(xué)底子在新式學(xué)堂里發(fā)芽金庸讀的是新式小學(xué),描紅卻是傳統(tǒng)路數(shù):顏柳打底,再上二王。查家規(guī)矩大,逢年過(guò)節(jié)要寫(xiě)“祖宗單”,祖父查文清在旁督陣,稍有懈怠便是一聲咳嗽。少年查良鏞由此練出一手穩(wěn)準(zhǔn)狠的用筆,日后寫(xiě)《天龍八部》里“凌波微步”的輕靈,或許正得益于當(dāng)年懸腕時(shí)的“步法身法”。

二、家學(xué):從查升到查良鏞的“墨脈”查升的字是康熙朝“官方指定手書(shū)”,董其昌再傳,秀潤(rùn)中見(jiàn)骨力;查慎行以詩(shī)名世,手稿亦勁瘦。金庸小時(shí)候在祠堂里見(jiàn)過(guò)祖上真跡,只覺(jué)得“字像長(zhǎng)個(gè)子的人,站得直,不怕風(fēng)”。這份基因潛伏多年,終于在20世紀(jì)90年代爆發(fā)——他回故鄉(xiāng),一口氣為十幾處單位題字,筆筆都有“向上拔”的姿勢(shì),像要把字寫(xiě)回祖譜里去。

三、字里有江湖:結(jié)構(gòu)、用筆與“俠氣”細(xì)看金庸書(shū)法,結(jié)字修長(zhǎng),中宮緊收,樂(lè)魚(yú)體育官方網(wǎng)站長(zhǎng)橫、長(zhǎng)捺卻肆意甩出,如劍氣破空;線條爽利,起筆如刀切入鞘,收筆戛然而止,留白處殺氣暗涌。最典型是那件行書(shū)中堂:“桃花影里飛神劍,碧海潮生吹玉簫”,十四字一氣呵成,劍勢(shì)簫韻,互為攻防。旁人看是詩(shī)句,懂武的人能看出招式:長(zhǎng)橫是“橫掃千軍”,長(zhǎng)豎是“一柱擎天”,金沙電玩app飛白處正是“回風(fēng)拂柳”的破綻。

四、黃庭堅(jiān)的影子與“俠之大者”金庸并不諱言學(xué)過(guò)黃庭堅(jiān)。山谷道人長(zhǎng)槍大戟的開(kāi)張,被他化進(jìn)自家筆底,卻濾掉山谷的拗怒,添了幾分溫潤(rùn)。有人問(wèn)他為何不像沈鵬那樣寫(xiě)連綿草,他笑答:“草書(shū)太像輕功,我怕讀者找不到落點(diǎn)。”于是我們看到一種“楷行相間”的自家體:行筆帶草意,結(jié)構(gòu)卻是楷書(shū)的穩(wěn),像張無(wú)忌的乾坤大挪移,外松內(nèi)緊,收放自如。落款常鈐一方小印——“為國(guó)為民”,四字縮成寸許,卻壓得整張紙沉下來(lái),那是他寫(xiě)字的“丹田”。

五、墨與潮:在海寧讀金庸字的正確姿勢(shì)故居窗外便是錢(qián)塘江,潮聲隱隱。展廳燈光下,那幅“浩氣長(zhǎng)存”四字斗方仿佛帶著水汽。講解員說(shuō),先生當(dāng)年鋪紙揮毫,一定要開(kāi)窗聽(tīng)潮,“潮頭近時(shí)落筆最疾,潮頭遠(yuǎn)時(shí)收筆最穩(wěn)”。于是墨色的干濕、線條的疾徐,暗合了江潮的呼吸——這是海寧才有的獨(dú)家音效。

六、尾聲:字與人,俱歸江湖金庸晚年最后一次回鄉(xiāng)題字,寫(xiě)的是“書(shū)香劍氣”。寫(xiě)完擲筆大笑:“字寫(xiě)完了,我也該回桃花島了。”如今墨跡已懸在展廳盡頭,玻璃反射出觀眾的身影,一時(shí)分不清是讀者還是俠客。墨香里,忽然懂了:他寫(xiě)的從來(lái)不是武俠,是用筆在江湖里刻下坐標(biāo)——“為國(guó)為民”四字,是郭靖的拳;“桃花影里飛神劍”,是黃藥師的簫;而那一筆筆挺拔的豎畫(huà),是他自己——站在潮頭,衣袂當(dāng)風(fēng),字如其人,俠如其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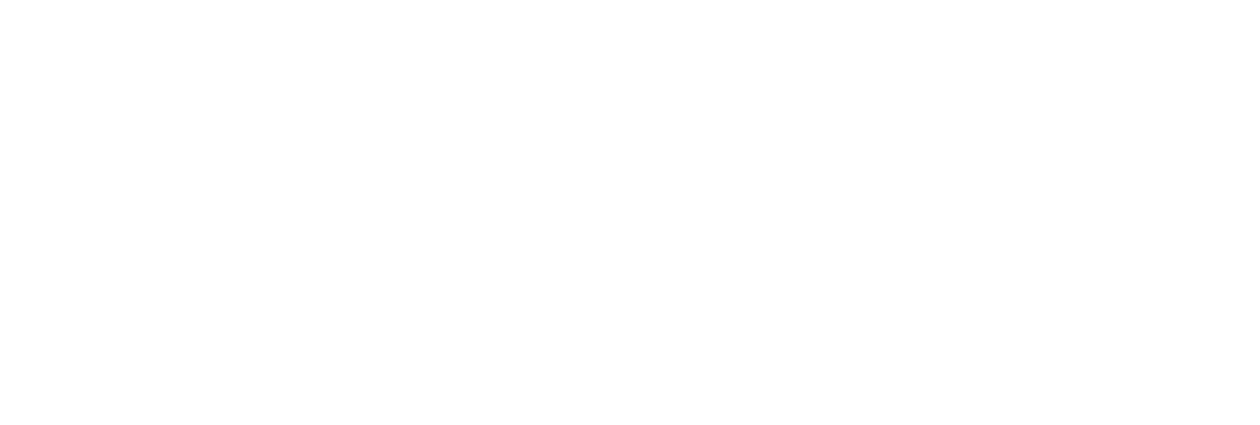

 備案號(hào):
備案號(hào):